鸡山小调
2025年09月15日
字数:4,368
版次:04
牛旭斌

山,万古不动,黄土堆积的,石头堆砌的,各有各的面目,又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重峦叠嶂,是山的姿态,高耸入云,是山的气势,巍然屹立,是山的风骨,群峰罗列,是山的韵味,奇石嶙峋,是山的神情,但一个样子的青绿,如被一场新雨洗过。
为避开城市的喧闹,我曾和朋友在闲暇时,顺山脚下的几道塬坡走过两回,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好朋友从外地回家探亲,我们携家带口,团聚山下他家。这山,地图上称“鸡峰山”,成县人都称“鸡山”。
吃过午饭,我们决定上山走走。在从农家乐出来的路口,我看见几片长势旺盛的小麦,郁郁葱葱。这五月的乡村,冬小麦度过了漫长寒冬,正当抽穗扬花时,所有的麦子都已挺直腰身,等待烈日炎炎的好天气熟麦。瞧,一山庄稼集体进入渐次成熟的最美年华。在滚滚红尘中来来往往的我们,面对稔熟于生命的麦子,没有什么事物,比眼前的青麦更动人。
从小在夏家塆山坳里长大,每到麦子灌浆麦粒饱满之前的这个季节,我们一帮伙伴点一堆小火烧麦吃,青麦穗放在火焰上燎,当麦衣被烧焦的时候,把燎青麦放在手心,两个手掌用力一搓,带着火巴的青麦粒,便老远飘散出烤洋芋般熟透的甜香。
太阳已经过了中午,鸡山下的田野间,我们被大山拥抱入怀,大山也能被我们一抱子揽入怀中。搂着吹过麦田的风,我举起手机,拍下了这些麦子,这青青翠翠的麦穗,就是养活我们的粮食,国徽上的那颗麦穗,就是我镜头中的麦子。等到小满过后,它们熟弯下头时,跟随麦场迁徙的“旋黄鸟”就来催促收割了:“旋黄旋割,四川的麦子割倒了,旋黄旋割,四川的麦子割倒了。”
爬到山脚,但见北麓如削,壁立千仞,一道横屏,连峰成岭。嵋峈峰就像矗立成县大地的望柱,被无边蔓延的青碧簇拥着,抬举着,耸立成一座参天的孤峰,而成为成县人心中的精神地标,成县人心目中的父亲山。穹庐起云,广播电视塔在变幻迭起的烟波间闪着金属的银光,青白石头的崖壁上,常年积雨生出的苔藓,看上去像画家泼下来的一道道浓墨。
天地被鸡山顶立,朝迎日出,暮送夕阳,栉风沐雨,万物从此酝酿和创造,就像一位可以信仰终生的慈父。高山巍巍的四野里,天高地阔,山明岭秀,浓荫匝地。鸡山耸入云端,无碍无累。漫山遍野的花草迎风,阳光闪烁,小鸟带路,树影迷离。
驱车至鸡山脚下,我们弃车独行,尽情地领略脱缰般无羁的山野,庄稼茂盛,坡场蓊郁,沿途的光影与花草,独具春天才有的美好。对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草,它芬芳的香味已入我的鼻息已润我的心肺,我感觉名字就在嘴边呼之欲出,却一急怎么也叫不上来,心里多少有些愧对和辜负的歉意;一些一口就能喊出名字的花草,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受宠若惊而打扰到它。姹紫嫣红的花团锦簇里,让鸡山脚下的山野和村庄,在晚春时节变成一个芬芳的秘境,让我产生恍入大梦不忍离舍的幻觉。
俯瞰广袤无垠的成县盆地,山原河谷、城市小镇、村舍厂企尽收眼底。西望丰泉山,东到成县机场的店村,四十多里川坝平畴生机盎然,几百座沃野丘陵连绵起伏,两条玉带般潺潺奔流的大河,手挽着手同归于飞龙峡谷。
风来时,我抬头仰望龙洞,仰望二梁子,仰望群山之巅的嵋峈峰,殿宇楼台,层层级级,千年古刹,钟磬悠悠,云遮雾罩的远山披着钢蓝色的黛蓑,舞动着碧绿的绸缎,天马行空的鸟儿只朝着高高的山峦飞去,体态雄健。当蒸腾的云雾被风追赶,过一会儿,便见太阳钻出云缝,照到半山和山顶上,出现一道道让人心灵为之感动和安详的金光。
在山梁上的另一个路口,我遇到一群脸上挂着汗珠手中拄着柴杖,身穿一身运动装朝山游山的人们,他们放怀山林,沿着小路,穿过荒野、田园,绕过清泉、菜籽地,他们不论是结伴而行,还是孤身独旅,他们不屈不挠地爬山,追求和享受这份登山乐趣的酣畅淋漓,不就是怀揣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的情怀吗?我向他们致敬,也想起曾经的我,也有过这般极像回事的执着与勇敢刚强的坚韧。而这距离我第一次随母亲赶庙会登鸡山烧香,已经过去了三十几个年头。那一年,我差一年就要考学,祖母安排母亲带我上山敬香,我逢香烧香,见佛就拜,遇庙就磕头。
依山而居住在山下村庄里的人们,深谙山对人的恩惠,最懂怎么样去接纳远方的宾朋,山脚下办起了七八户农家乐,庭院栽竹种花,搭亭砌灶,柴火鸡在铁锅里咕咕嘟嘟地煮着,一阵油爆葱花的香味,沁人心脾地飘荡过山麓下的人家和竹林。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但渴望挣脱种种内卷与消耗的“枷锁”,渴望走进还能看看炊烟看看大山的田园,诗意地栖居。来到鸡山下的人们,心情飞扬,是因为山花烂漫的濡染,歌声飘荡,是受到大自然里万物葱茏的感动。十里飘香的七里香,是我儿时掐掰刺蕻的刺架,白色的花朵,在风中抖落一地的浪花。
迎春与腊梅在此交接,樱花与杏花次第怒放,阡陌纵横,曲径通幽,花红柳绿,芳草连天,鸟语花香,几十种上百种的草木之花,排着队等着游人来观赏。山里的花儿或是草药,丛丛簇簇,一畦畦沿沟沿坎天然生长,依着二十四节气不慌不忙,应节而生,开花结果,组成了村庄一年四季里独有的接连不断的花事。
漫无尽头的群山,一山更比一山高。此时此刻,我们就在鸡山下,就在草木葳蕤的橡树林中,就在清风作伴的庄稼地旁,我多想有一头牛,再举起皮鞭,在这绿得没有边际的山坡上,吹起柳叶做的口哨,用通花秆草的茎髓曲成玩具,用款冬花草的叶子做成一顶太阳伞戴在头上,这些都是历经世场厌倦,而藏匿于人心深处永不泯灭返璞归真的对纯朴自然生活的顾恋与追寻。在这样与世可以了望与纷扰暂且相隔的鸡山脚下,八方静谧,草木吐绿,万木萧萧,心绪将息,倦鸟逐人,鸡犬相闻,人心淡定,缄默如山,静美的天地恍如一个待回答的谜。
成县没有县树,因为这方厚土的有容乃大,树种过多。遍地生长的一千九百多种植物,除了珍贵的楠木、红豆杉等树种之外,在成县,梅兰松竹,大有座座山林可寻见的身影。而常常用来包围、保护和捍卫村庄的树木,是高耸参天的大白杨,是满地皆是的核桃树,在村头高岗庙梁上远远就可望见的大树,往往是一棵苍柏,一棵铁匠树,它们是守望村庄经过百年风雨的古树,特别巨大而醒目,高耸而苍老,有些村庄奉树为神,有些孩子拜树为父(拜大),借树木之灵气,了还和补偿某种心愿。在嵋峈峰周围,生长着几棵铁匠树,树枝上挂满游客的祈福。
铁匠树,学名刺叶高山栎,属于壳斗科栎属树种,其材质坚硬,常用于制作木匠的推刨、农具柄把等。唐开国功臣尉迟敬德是成县大地上家喻户晓的人物,被后世尊为“门神”的他,奉旨在鸡峰山建造佛寺时,这棵铁匠树已经有胳膊般粗了。而今,长在山脊上的老树,根深叶茂,树冠蓬勃,苍翠欲滴,万古长青。
来过鸡峰山的历史名人中,有这么五个人,值得细说。一是秦始皇,他在灭六国的第二年,即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所干的一件大事是“西巡祭祖”,时年39岁。《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清乾隆六年编撰的《成县新志》也记载:“史称秦始皇西巡,登鸡头山,命宫娥吹箫,使长子扶苏兼蒙恬军。”从秦始皇西巡的目的看,祭祖是不容怀疑的。鸡峰山正好位处秦国西垂故地范围,特别是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发现,已经完全证实了史书记载嬴秦故都邑在今西汉水上游地区,即古西垂之地。在古人心目中,天地、先祖是神圣的。所以,秦始皇灭六国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到西陲故地祭奠先祖。秦民族又是信仰图腾的民族,成县周围传承下来的地名、水名中,就有鸡峰山、凤凰山、黄鹿坡、卧虎崖、飞龙峡、鹿玉山等,见证了先人们自古敬畏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之道和智慧。这位登临过鸡峰山的第一位皇帝,是大一统王朝的创造者,是中央集权制的开创者,是世界奇迹万里长城的修筑者,因为他的来过,鸡峰山从此成为秦皇祭天的圣地,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二是汉武帝,《成县新志》称:“汉武帝过回中,登崆峒,至鸡头山。”三是唐太宗曾登鸡山,相传唐太宗李世民狩猎避暑时也登临过此山,山上至今有唐王阁遗址确是事实。四是流传着尉迟敬德建造鸡峰山佛寺并记载其事迹的故事。
第五个是备兵陇右的燕台七子、清八大诗家之一的宋琬,他让成县鸡峰山为世人所知。那时,宋琬任职秦州。古称的秦州,即如今的天水。出于对杜甫崇拜和情有独钟,宋琬为杜甫精湛的诗艺所倾倒,又感同身受于他悲惨的身世际遇,与自己相似,而成为跨代穿越的“忘年交”。高山流水遇知音,顺治七年(1650年),他在狱中就写了著名的《庚寅腊月读子美同谷七歌效其体以咏哀》,悲凉凄怆,类似杜甫陇右写于同谷的诗歌。同谷之地,就是今天的成县。当年,他一到秦州之后,接连两次拜访成县杜工部草堂。他在《题杜子美秦州流寓诗石刻后》中曾写道:“余小子备官天水,拜先生之祠宇而新之。尝两登成州之凤凰台,其下有飞龙峡,先生之草堂在焉。”顺治十一年(1654年)初冬,他同友人成县知县欧阳介庵拜访杜甫草堂,登成县之凤凰台,并写了《同欧阳介庵拜杜子美草堂》,他还和欧阳介庵筹划重修草堂,并作了《祭杜少陵草堂文》拜祭这位伟大的诗人。在此期间,他特意登临当时名扬秦陇巴蜀的鸡峰山,夜宿鸡山,写下《宿鸡山寺》三首,流传千古。这位文士,视杜诗为宗,一生膜拜,登到鸡山上,他在其一中惊叹“天外群峰小,云端板屋牢”,在其二中赞美“松声长似雨,峦气自成烟”,在其三中感慨“看山心倍勇,闻磐夜何清。羡尔仇池长,频来屐齿轻。”秦皇汉武,唐王清臣,屡临鸡山,还有学者研究认为,早在公元36年,鸡山上就有佛教传播,释道儒归于一山的包容,让成县在历史长河的演进与淘漉中,没有被淹没,而自带光芒和文雅异彩。
就是不知何故,曾经一度香火旺盛摩肩接踵的寺观庙刹,在这些年为何陷入了沉寂,山路上很少看见登山朝山的人。好在乡村振兴的春风,已经吹绿了山脚下沉睡的村庄,外地创业的人也回乡了,年久失修的民居修葺一新,村村巷巷的道路环环弯弯,垂钓,采摘,踏青,美食,民俗体验,应有尽有,崇尚耕读传家、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蔚然成风。鸡山下仍然以乡土为根基的人们,用新时代的眼光,寻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自然呼应,获取人在守护青山绿水中才会有的生态红利。
五一前夕,抛沙镇小湾村,自驾游的人们成群结队,纷至沓来,越来越多的城里人盼望回归自然,渴求在青山绿水的田园式牧歌里润泽心灵。听,是谁在唱:“天黑时麻雀寻窝哩,罐罐的拌汤给我喝哩。罐罐儿里提的酸拌汤,拌汤还没喝就把人看上。”
这是多么朴素的心思呀,又是一种多么两情相悦的情和意,这是山里人心有灵犀的盼念和表白呀!
生在鸡山脚下的乡亲们,也曾经因被大山重围光景不好而抱怨过,绝望过。如今,他们又为能住在这样一个地方,能天天仰靠和倚仗大山而窃喜而幸福。随着大景区规划的落地,鸡山沿麓的环线开发,必将让他们的日子更加红红火火。勤劳的他们,其实已经提前过上了城里人向往的诗意栖居的生活。相信不远的一天,小湾村和鸡山的风华绝美将被世人众所皆知。
一种花就是一个词牌,一座炊烟升起的房屋就是一曲小调。夜幕降临时,我走出小湾村,村口就是高速公路的互通立交。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数字报首页
数字报首页 上一期
上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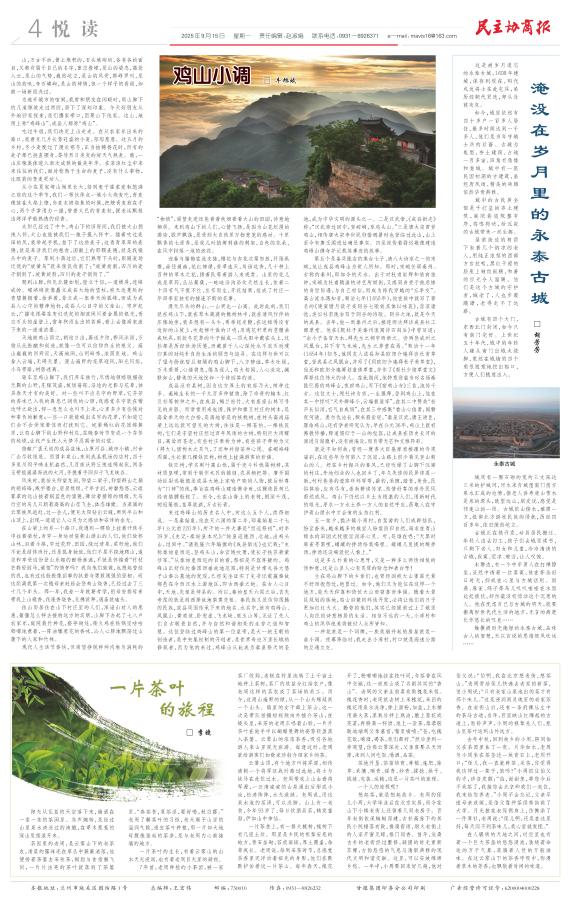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